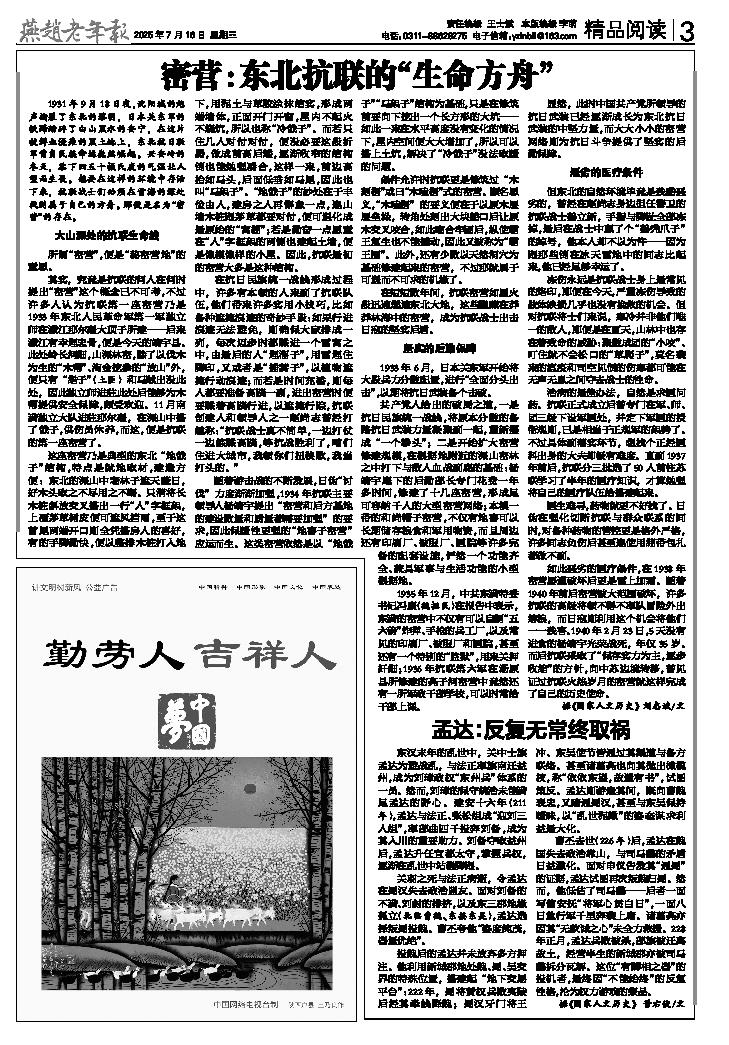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的炮声撕裂了东北的黎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碎了白山黑水的安宁,在这片被鲜血浸染的黑土地上,东北抗日联军背负民族命运巍然崛起。兴安岭的冬天,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气温让人望而生畏。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存活下来,抗联战士们必须在雪海的深处找到属于自己的方舟。那便是名为“密营”的存在。
大山深处的抗联生命线
所谓“密营”,便是“秘密营地”的意思。
其实,究竟是抗联的何人在何时提出“密营”这个概念已不可考,不过许多人认为抗联第一座密营乃是1933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濛江那尔轰大顶子所建——后来濛江有幸埋忠骨,便是今天的靖宇县。此处岭长河细,山深林密,除了以伐木为生的“木帮”、淘金挖参的“放山”外,便只有“绺子”(土匪)和马贼出没此处,因此独立师进驻此处后能够为木帮提供安全保障,颇受欢迎。11月南满独立大队进驻那尔轰,在深山中搭了戗子,供伤员休养,而这,便是抗联的第一座密营了。
这座密营乃是典型的东北“地戗子”结构,特点是就地取材,建造方便:东北的深山中老林子遮天蔽日,好木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消将长木桩斜放交叉搭出一行“人”字框架,上覆茅草树皮便可遮风挡雨,至于这首尾两端开口则全凭搭房人的喜好,有的手脚勤快,便以整排木桩打入地下,用泥土与草胶涂抹结实,形成两端墙体,正面开门开窗,屋内不起火不烧炕,所以也称“冷戗子”。而若只住几人对付对付,便没必要这般折腾,做成前高后矮,逐渐收窄的结构倒也能勉强凑合,这样一来,前边高抬如马头,后面低垂如马尾,因此也叫“马架子”。“地戗子”的妙处在于丰俭由人,建房之人再懈怠一点,连山墙木桩跟茅草都要对付,便可退化成最原始的“窝棚”;若是勤奋一点愿意在“人”字框架的两侧也建起土墙,便是像模像样的小屋。因此,抗联最初的密营大多是这种结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许多有本领的人来到了抗联队伍,他们带来许多实用小技巧,比如各种遮掩痕迹的奇妙手段:如果行进痕迹无法避免,则确保大家排成一列,每次迈步时都踩进一个雪窝之中,由最后的人“埋溜子”,用雪埋住脚印,又或者是“插蒿子”,以植物遮掩行动痕迹;而若是时间充裕,则每人都要准备高跷一副,进出密营时便要踩着高跷行进,以遮掩行踪,抗联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赵尚志曾经打趣称:“抗联战士真不简单,一边打仗一边练踩高跷,等抗战胜利了,咱们住进大城市,我领你们扭秧歌,我当打头的。”
随着游击战的不断发展,日伪“讨伐”力度渐渐加强,1934年抗联主要领导人杨靖宇提出“密营和后方基地的建设数量和质量都需要加强”的要求,因此保暖性更强的“地窖子密营”应运而生。这类密营依然是以“地戗子”“马架子”结构为基础,只是在修筑前要向下挖出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如此一来在水平高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屋内空间便大大增加了,所以可以搭上土炕,解决了“冷戗子”没法取暖的问题。
条件允许时抗联更是修筑过“木刻楞”或曰“木嗑楞”式的密营。顾名思义,“木嗑楞”的要义便在于以原木层层垒垛,转角处刻出大块豁口后让原木交叉咬合,如此吻合牢固后,纵使霸王复生也不能撼动,因此又被称为“霸王圈”。此外,还有少数以天然洞穴为基础修建起来的密营,不过那就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了。
在短短数年间,抗联密营如星火般迅速燃遍东北大地,这些隐藏在莽莽林海中的密营,成为抗联战士出击日寇的坚实后盾。
坚实的后勤保障
1933年6月,日本关东军开始将大股兵力分散配置,进行“全面分头出击”,以期将抗日武装各个击破。
共产党人给出的破局之道,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原本分散的各路抗日武装力量凝聚到一起,重新攥成“一个拳头”;二是开始扩大密营修建规模,在根据地附近的深山密林之中打下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基础:杨靖宇麾下的后勤部长专门花费一年多时间,修建了十几座密营,形成足可容纳千人的大型密营网络;本溪一带的和尚帽子密营,不仅有地窖可以长期储存粮食和军用物资,而且周边还有印刷厂、被服厂、医院等许多完备的配套设施,俨然一个功能齐全、兼具军事与生活功能的小型根据地。
1935年12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报告中表示,东满的密营中不仅有可以自制“五六磅”炸弹、手枪的兵工厂,以及常见的印刷厂、被服厂和医院,甚至还有一个特别的“监狱”,用来关押奸细;1936年抗联第六军在汤原县所修建的亮子河密营中竟然还有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可以时常给干部上课。
显然,此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逐渐成长为东北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而大大小小的密营网络则为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恶劣的医疗条件
但东北的自然环境毕竟是残酷恶劣的,曾经在赵尚志身边担任警卫的抗联战士姜立新,手指与脚趾全部冻掉,最后在战士中赢了个“姜秃爪子”的绰号,他本人却不以为忤——因为跟那些倒在冰天雪地中的同志比起来,他已经足够幸运了。
冻伤永远是抗联战士身上最常见的烙印,即便在今天,严重冻伤导致的肢体缺损几乎也没有挽救的机会。但对抗联将士们来说,寒冷并非他们唯一的敌人,即便是在夏天,山林中也存在着致命的威胁:聚散成团的“小咬”、叮住就不会松口的“草爬子”,莫名袭来的瘟疫和司空见惯的伤寒都可能在无声无息之间夺去战士的性命。
治病的最佳办法,自然是求医问药。抗联正式成立后曾专门在军、师、团三级下设军医处,并定下军医的授衔规则,已是相当于正规军的架势了。不过具体到落实环节,想找个正经医科出身的大夫却极有难度。直到1937年前后,抗联分三批选了50人前往苏联学习了半年的医疗知识,才算勉强将自己的医疗队伍给搭建起来。
医生难寻,药物就更不好找了。日伪在强化切断抗联与群众联系的同时,对各种药物的管控更是格外严格,许多同志负伤后甚至连使用绷带包扎都做不到。
如此恶劣的医疗条件,在1938年密营屡遭破坏后更是雪上加霜。随着1940年前后密营被大范围破坏,许多抗联的高级将领不得不率队冒险外出筹粮,而日寇则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们一一残害。1940年2月23日,5天没有进食的杨靖宇光荣战死,年仅35岁。而后抗联采取了“保存实力为主,逐步收缩”的方针,向中苏边境转移,曾见证过抗联火热岁月的密营就这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据《国家人文历史》 刘志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