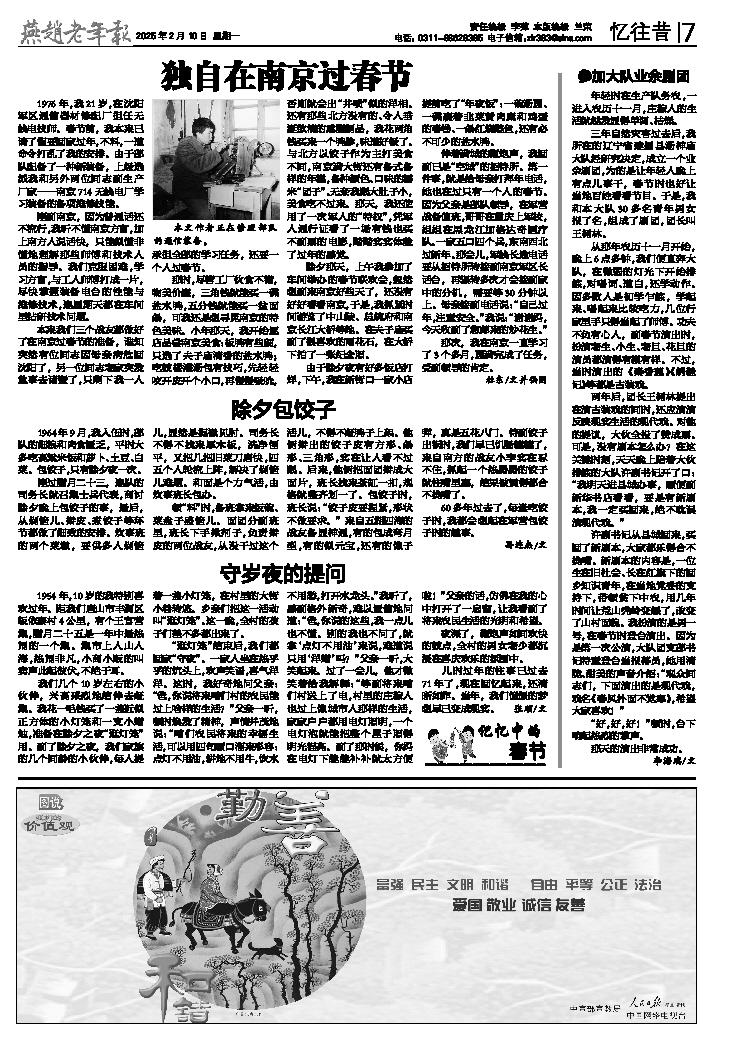1976年,我21岁,在沈阳军区通信器材修配厂担任无线电技师。春节前,我本来已请了假要回家过年,不料,一道命令打乱了我的安排。由于部队配备了一种新装备,上级选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到生产厂家——南京714无线电厂学习装备的各项维修技能。
刚到南京,因为普通话还不流行,我听不懂南京方言,加上南方人说话快,只能似懂非懂地理解那些师傅和技术人员的指导。我们克服困难,学习方言,与工人师傅打成一片,尽快掌握装备电台的性能与维修技术,连星期天都在车间里钻研技术问题。
本来我们三个战友都做好了在南京过春节的准备,谁知突然有位同志因母亲病危回沈阳了,另一位同志老家突发急事去诸暨了,只剩下我一人承担全部的学习任务,还要一个人过春节。
那时,尽管工厂伙食不错,物美价廉,三角钱就能买一碟盐水鸭,五分钱就能买一盆面条,可我还是想寻觅南京的特色美味。小年那天,我开始逐店品尝南京美食:板鸭有些硬,只选了夫子庙清香的盐水鸭;吃鼓楼灌汤包有技巧,先轻轻咬开皮开个小口,再慢慢吸吮,否则就会出“井喷”似的洋相。还有那些北方没有的、令人垂涎欲滴的熏腊制品,我花两角钱买来一个鸭胗,味道好极了。与北方以饺子作为主打美食不同,南京满大街还有各式各样的年糕,各种颜色、口味的糯米“团子”。无奈我眼大肚子小,美食吃不过来。那天,我还使用了一次军人的“特权”,凭军人通行证看了一场有钱也买不到票的电影,踏踏实实体验了过年的感觉。
除夕那天,上午我参加了车间举办的春节联欢会,忽然想到来南京好些天了,还没有好好看看南京,于是,我抓紧时间游览了中山陵、总统府和南京长江大桥等地。在夫子庙买到了很喜欢的雨花石,在大桥下拍了一张纪念照。
由于除夕夜有好多饭店打烊,下午,我在新街口一家小店提前吃了“年夜饭”:一碗汤圆、一碟裹着韭菜黄肉糜和鸡蛋的春卷、一条红烧鲢鱼,还有必不可少的盐水鸭。
伴着满城的鞭炮声,我回到已是“空城”的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打拜年电话,她也在过只有一个人的春节。因为父亲是部队领导,在军营战备值班,哥哥在重庆上军校,姐姐在黑龙江加格达奇医疗队。一家五口四个兵,东南西北过新年。那会儿,军线长途电话要从招待所转接到南京军区长话台,再辗转多次才会接到家中的分机,需要等30分钟以上。母亲接到电话说:“自己过年,注意安全。”我说:“谢谢妈,今天收到了您邮来的炒花生。”
那次,我在南京一直学习了3个多月,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领导的肯定。
杜东/文并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