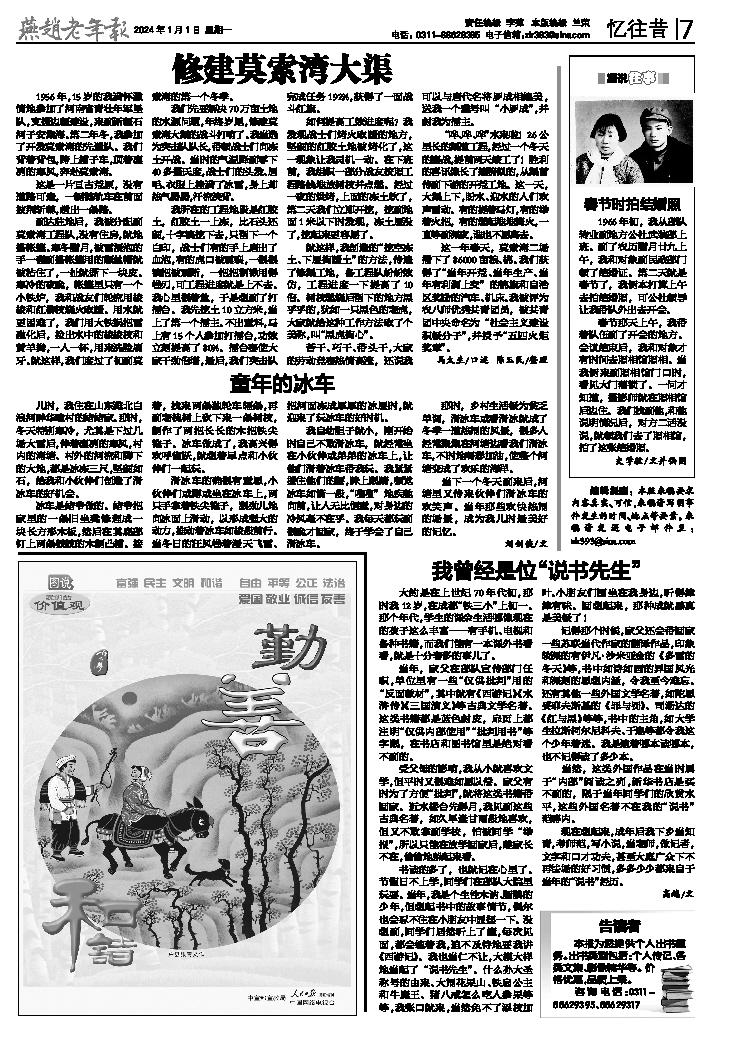大约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12岁,在成都“铁三小”上初一。那个年代,学生的课余生活哪像现在的孩子这么丰富——有手机、电视和各种书籍,而我们能有一本课外书看看,就是十分奢侈的事儿了。
当年,家父在部队宣传部门任职,单位里有一些“仅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其中就有《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这类书籍都是蓝色封皮,扉页上都注明“仅供内部使用”“批判用书”等字眼,在书店和图书馆里是绝对看不到的。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但平时又很难如愿以偿。家父有时为了方便“批判”,就将这类书籍带回家。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见到这些古典名著,如久旱逢甘雨般地喜欢,但又不敢拿到学校,怕被同学“举报”,所以只能在放学回家后,趁家长不在,偷偷地躲起来看。
书读的多了,也就记在心里了。节假日不上学,同学们在部队大院里玩耍。当年,我是个生性木讷、腼腆的少年,但想起书中的故事情节,偶尔也会忍不住在小朋友中显摆一下。没想到,同学们居然听上了瘾,每次见面,都会缠着我,迫不及待地要我讲《西游记》。我也当仁不让,大模大样地当起了“说书先生”。什么孙大圣称号的由来、大闹花果山、铁扇公主和牛魔王、猪八戒怎么吃人参果等等,我张口就来,当然免不了添枝加叶。小朋友们围坐在我身边,听得津津有味。回想起来,那种成就感真是美极了!
记得那个时候,家父还会带回家一些苏联当代作家的翻译作品,印象较深的有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等,书中如诗如画的异国风光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令我至今难忘。还有其他一些外国文学名著,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书中的主角,如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于连等都令我这个少年着迷。我是逮着哪本读哪本,也不记得读了多少本。
当然,这类外国作品在当时属于“内部”阅读之列,新华书店是买不到的,限于当年同学们的欣赏水平,这些外国名著不在我的“说书”范畴内。
现在想起来,成年后我下乡当知青,考师范,写小说,当老师,做记者,文字和口才功夫,甚至大庭广众下不再怯场的好习惯,多多少少都来自于当年的“说书”经历。
高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