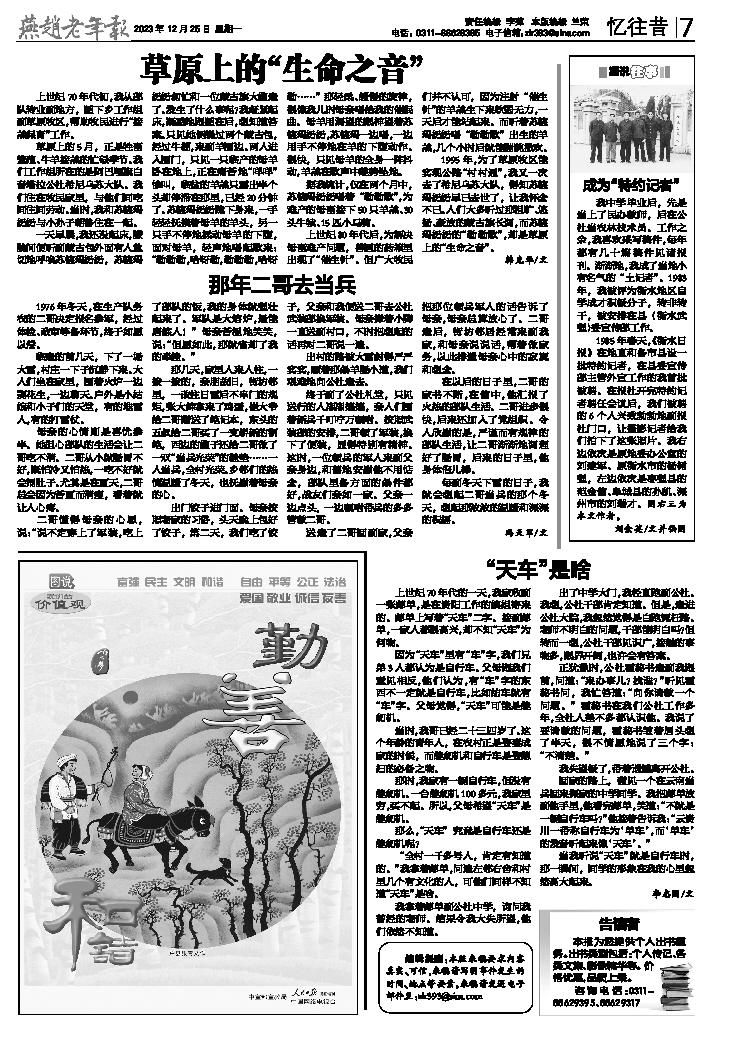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随下乡工作组到草原牧区,帮助牧民进行“接羔保育”工作。
草原上的5月,正是牲畜繁殖、牛羊接羔的忙碌季节。我们工作组所在的是阿巴嘎旗白音塔拉公社希尼乌苏大队。我们住在牧民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和苏德玛奶奶与小孙子朝鲁住在一起。
一天早晨,我还没起床,朦胧间便听到蒙古包外面有人急切地呼唤苏德玛奶奶,苏德玛奶奶匆忙和一位蒙古族大嫂走了。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赶紧起床,疑惑地跟随在后,想知道答案。只见她俩绕过两个蒙古包,经过牛棚,来到羊圈边。两人进入圈门,只见一只临产的母羊卧在地上,正在痛苦地“咩咩”惨叫,临盆的羊羔只露出半个头却停滞在那里,已经20分钟了。苏德玛奶奶跪下身来,一手轻轻抚摸着母羊的羊头,另一只手不停地揉动母羊的下腹,面对母羊,轻声地唱起歌来:“勒勒勒,哈呀勒,勒勒勒,哈呀勒……” 那轻柔、缓慢的旋律,很像我儿时母亲唱给我的催眠曲。母羊用渴望的眼神望着苏德玛奶奶,苏德玛一边唱,一边用手不停地在羊的下腹动作。很快,只见母羊的全身一阵抖动,羊羔在歌声中趁势坠地。
据我统计,仅在两个月中,苏德玛奶奶唱着“勒勒歌”,为难产的母畜接下50只羊羔、30头牛犊、15匹小马驹。
上世纪80年代后,为解决母畜难产问题,兽医的药箱里出现了“催生针”。但广大牧民们并不认可,因为注射“催生针”的羊羔生下来软弱无力,一天后才能站起来。而听着苏德玛奶奶唱“勒勒歌”出生的羊羔,几个小时后就能蹦跳撒欢。
1995年,为了草原牧区能实现公路“村村通”,我又一次去了希尼乌苏大队,得知苏德玛奶奶早已去世了,让我怀念不已。人们大多听过那粗旷、悠扬、豪放的蒙古族长调,而苏德玛奶奶的“勒勒歌”,却是草原上的“生命之音”。
韩克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