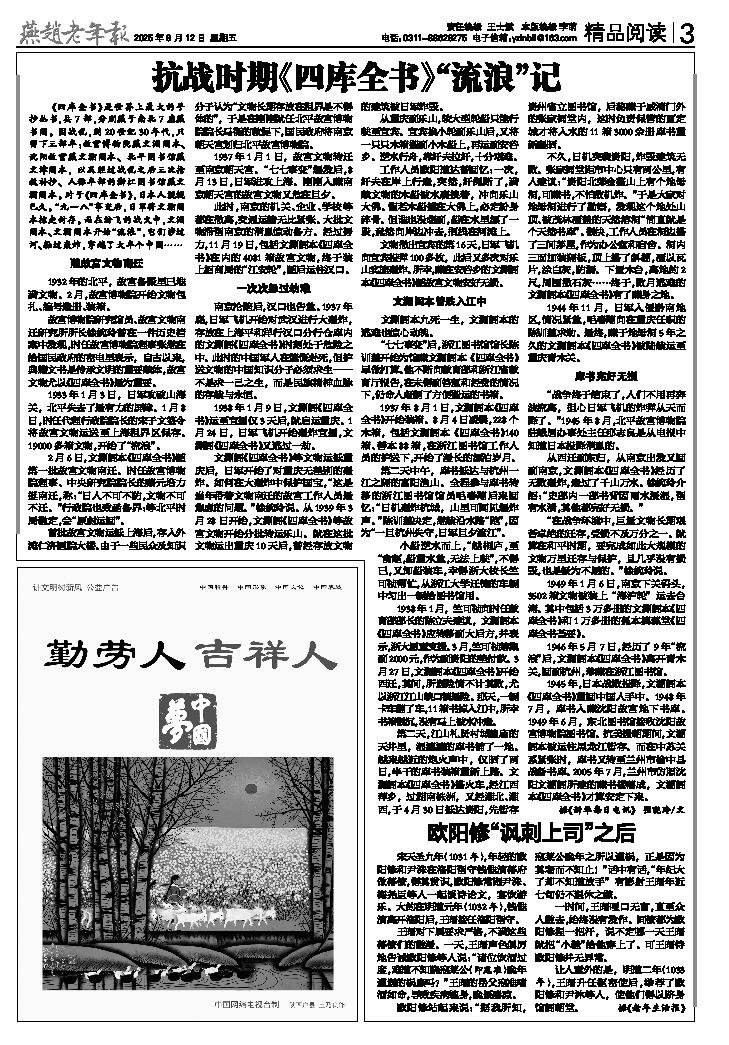《四库全书》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抄丛书,共7部,分别藏于南北7座藏书阁。因战乱,到20世纪30年代,只留下三部半:故宫博物院藏文渊阁本、沈阳故宫藏文溯阁本、北平图书馆藏文津阁本,以及经过战乱之后三次抢救补抄、人称半部的浙江图书馆藏文澜阁本。对于《四库全书》,日本人觊觎已久。“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将文溯阁本掠走封存。而在纷飞的战火中,文渊阁本、文澜阁本开始“流浪”,它们涉过河、躲过轰炸,穿越了大半个中国……
随故宫文物南迁
1932年的北平,故宫各殿里已堆满文物。2月,故宫博物院开始文物包扎、编号造册、装箱。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所长徐婉玲曾在一件历史档案中发现,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张继在给国民政府的密电里表示,自古以来,典籍文书是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故宫文物尤以《四库全书》最为重要。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破山海关,北平失去了最有力的屏障。1月8日,时任代理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签令将故宫文物运送至上海租界区保存。19000多箱文物,开始了“流浪”。
2月6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随第一批故宫文物南迁。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力挺南迁,称:“日人不可不防,文物不可不迁。”行政院也致函各界:等北平时局稳定,会“原封运回”。
首批故宫文物运抵上海后,存入外滩仁济医院大楼。由于一些民众及知识分子认为“文物长期存放在租界是不得体的”,于是在刚刚就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敦促下,国民政府将南京朝天宫划归北平故宫博物院。
1937年1月1日,故宫文物转迁至南京朝天宫。“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刚刚入藏南京朝天宫的故宫文物又危在旦夕。
此时,南京的机关、企业、学校等都在撤离,交通运输无比紧张。大批文物滞留南京的消息惊动各方。经过努力,11月19日,包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在内的4081箱故宫文物,终于装上招商局的“江安轮”,随后运往汉口。
一次次躲过劫难
南京沦陷后,汉口也告急。1937年底,日军飞机开始对武汉进行大轰炸,存放在上海平和洋行汉口分行仓库内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此时的中国军人在慷慨赴死,但护送文物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求生——不是求一己之生,而是民族精神血脉的存续与永恒。
1938年1月9日,文渊阁《四库全书》运至宜昌仅3天后,就启运重庆。1月24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宜昌,文渊阁《四库全书》又逃过一劫。
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文物运抵重庆后,日军开始了对重庆无差别的轰炸。如何在大轰炸中保护国宝,“这是当年带着文物南迁的故宫工作人员最焦虑的问题。”徐婉玲说。从1939年3月28日开始,文渊阁《四库全书》等故宫文物开始分批转运乐山。就在这批文物运出重庆10天后,曾经存放文物的建筑被日军炸毁。
从重庆到乐山,较大型轮船只能行驶至宜宾。宜宾换小轮到乐山后,又将一只只木箱搬到小木船上,再运到安谷乡。逆水行舟,靠纤夫拉纤,十分艰难。
工作人员欧阳道达曾回忆:一次,纤夫在岸上行走,突然,纤绳断了,满载文物的木船被水裹挟着,冲向乐山大佛。假若木船撞在大佛上,必定粉身碎骨。但谁也没想到,船在水里漂了一段,竟然向岸边冲去,搁浅在河滩上。
文物撤出宜宾的第16天,日军飞机向宜宾投弹100多枚,此后又多次对乐山实施轰炸。所幸,藏在安谷乡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随故宫文物安好无损。
文澜阁本曾跌入江中
文渊阁本九死一生,文澜阁本的逃难也惊心动魄。
“七七事变”后,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开始为馆藏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早做打算。他不断向教育部和浙江省教育厅报告,在未得到答复和经费的情况下,仍命人赶制了方便搬运的书箱。
1937年8月1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开始装箱。8月4日凌晨,228个木箱,包括文澜阁本《四库全书》140箱、善本88箱,在浙江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护送下,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岁月。
第二天中午,库书抵达与杭州一江之隔的富阳渔山。全程参与库书转移的浙江图书馆馆员毛春翔后来回忆:“日机轰炸杭城,山里可闻见爆炸声。”陈训慈决定,继续沿水路“跑”,因为“一旦杭州失守,日军旦夕渡江”。
小船逆水而上,“越桐庐,至“俞赵,船重水急,无法上驶”,不得已,又卸船装车,幸得浙大校长竺可桢帮忙,从浙江大学迁徙的车辆中匀出一辆给图书馆用。
1938年1月,竺可桢向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建议,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应转移到大后方,并表示,浙大愿意支援。3月,竺可桢筹集到2000元,作为到贵阳的垫付款。3月27日,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开始西迁,其间,所遇险情不计其数,尤以浙江江山峡口镇最险。那天,一辆卡车翻了车,11箱书掉入江中,所幸书箱很沉,没有马上被水冲走。
第二天,江山礼贤村城隍庙的天井里,湿漉漉的库书铺了一地。越来越近的炮火声中,仅晒了两日,半干的库书装箱重新上路。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搭火车,经江西萍乡,过湖南株洲,又经湘北、湘西,于4月30日抵达贵阳,先暂存贵州省立图书馆,后秘藏于威清门外的张家祠堂内,这时负责保管的夏定域才将入水的11箱3000余册库书重新曝晒。
不久,日机突袭贵阳,炸毁建筑无数。张家祠堂距市中心只有两公里,有人建议:“贵阳北郊金鳌山上有个地母洞,可藏书,不怕敌机炸。”于是大家对地母洞进行了勘察,发现这个地处山顶、被茂林覆盖的天然溶洞“简直就是个天然书库”。很快,工作人员在洞边搭了三间茅屋,作为办公室和宿舍。洞内三面加装隔板,顶上搭了斜棚,覆以瓦片,涂白灰,防漏。下置木台,离地约2尺,周围撒石灰……终于,数月逃难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有了藏身之地。
1944年11月,日军入侵黔南地区,情况紧急,毛春翔向在重庆任职的陈训慈求助。最终,藏于地母洞5年之久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被陆续运至重庆青木关。
库书完好无损
“战争终于结束了,人们不用再奔波流离,担心日军飞机的炸弹从天而降了。”1945年8月,北平故宫博物院驻峨眉办事处主任那志良是从电报中知道日本投降消息的。
从西迁到东归,从南京出发又回到南京,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历了无数轰炸,走过了千山万水。徐婉玲介绍:“史部内一部书背因雨水浸湿,留有水渍,其他都完好无损。”
“在战争环境中,巨量文物长期艰苦卓绝的迁存,受损不及万分之一。就算在和平时期,要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文物万里迁存与保护,且几乎没有损毁,也是极为不易的。”徐婉玲说。
1949年1月6日,南京下关码头,3502箱文物被装上“海沪轮”运去台湾。其中包括3万多册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和1万多册的孤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
1946年5月7日,经历了9年“流浪”后,文澜阁本《四库全书》离开青木关,回到杭州,珍藏在浙江图书馆。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重回中国人手中。1948年7月,库书入藏沈阳故宫地下书库。1949年6月,东北图书馆接收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抗美援朝期间,文溯阁本被运往黑龙江暂存。而在中苏关系紧张时,库书又转至兰州市榆中县战备书库。2005年7月,兰州市仿照沈阳文溯阁所建的藏书楼落成,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算安定下来。
据《新华每日电讯》 强晓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