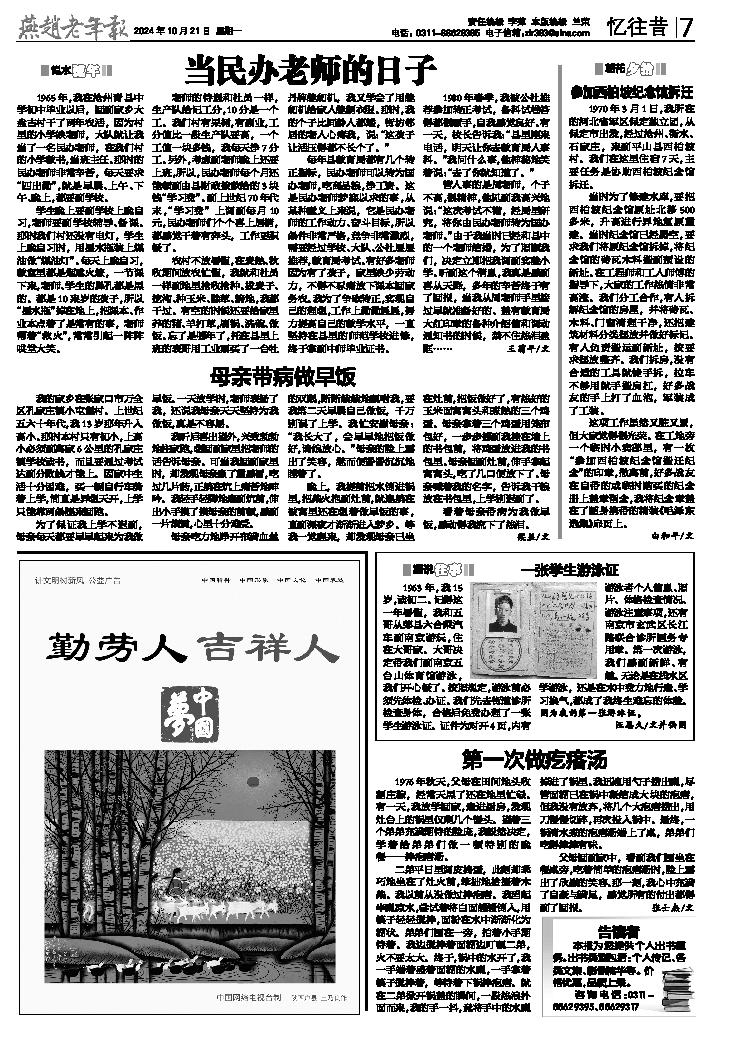1965年,我在沧州青县中学初中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大盘古村干了两年农活,因为村里的小学缺老师,大队就让我当了一名民办老师,在我们村的小学教书,当班主任。那时的民办老师非常辛苦,每天要求“四出勤”,就是早晨、上午、下午、晚上,都要到学校。
学生晚上要到学校上晚自习,老师要到学校辅导、备课。那时我们村还没有电灯,学生上晚自习时,用墨水瓶装上煤油做“煤油灯”。每天上晚自习,教室里都是烟熏火燎,一节课下来,老师、学生的鼻孔都是黑的。都是10来岁的孩子,所以“墨水瓶”掉在地上,把课本、作业本点着了是常有的事,老师帮着“救火”,常常引起一阵阵哄堂大笑。
老师的待遇和社员一样,生产队给记工分,10分是一个工。我们村有果树,有副业,工分值比一般生产队要高,一个工值一块多钱,我每天挣7分工。另外,考虑到老师晚上还要上班,所以,民办老师每个月还能领到由县财政拨款给的3块钱“学习费”。到上世纪70年代末,“学习费”上调到每月10元,民办老师们个个喜上眉梢,都感觉干着有奔头,工作更积极了。
农村不放暑假,在麦熟、秋收期间放农忙假,我就和社员一样到地里抢收抢种。拔麦子、挖沟、种玉米、除草、耪地,我都干过。有空的时候还要给家里养的猪、羊打草,刷锅、洗碗、做饭。忘了是哪年了,托在县里上班的表哥用工业票买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我又学会了用缝纫机给家人缝制衣服。那时,我的个子比同龄人都矮,街坊邻居的老人心疼我,说:“这孩子让活压得都不长个了。”
每年县教育局都有几个转正指标,民办老师可以转为国办老师,吃商品粮,挣工资。这是民办老师梦寐以求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民办老师的工作动力、奋斗目标,所以条件非常严格,竞争非常激烈,需要经过学校、大队、公社层层推荐,教育局考试。有好多老师因为有了孩子,家里缺少劳动力,不得不忍痛放下课本回家务农。我为了争取转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工作上勤勤恳恳,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一直坚持在县里的师范学校进修,终于拿到中师毕业证书。
1980年春季,我被公社推荐参加转正考试,各科试卷答得都很顺手,自我感觉良好。有一天,校长告诉我:“县里刚来电话,明天让你去教育局人事科。”我问什么事,他神秘地笑着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管人事的是周老师,个子不高,很精神,他见到我高兴地说:“这次考试不错,经局里研究,将你由民办老师转为国办老师。”由于我当时已经和县中的一个老师结婚,为了照顾我们,决定立即把我调到实验小学。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感到喜从天降,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回报,当我从周老师手里接过早就准备好的、盖有教育局大红印章的各种介绍信和调动通知书的时候,禁不住热泪盈眶……王菊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