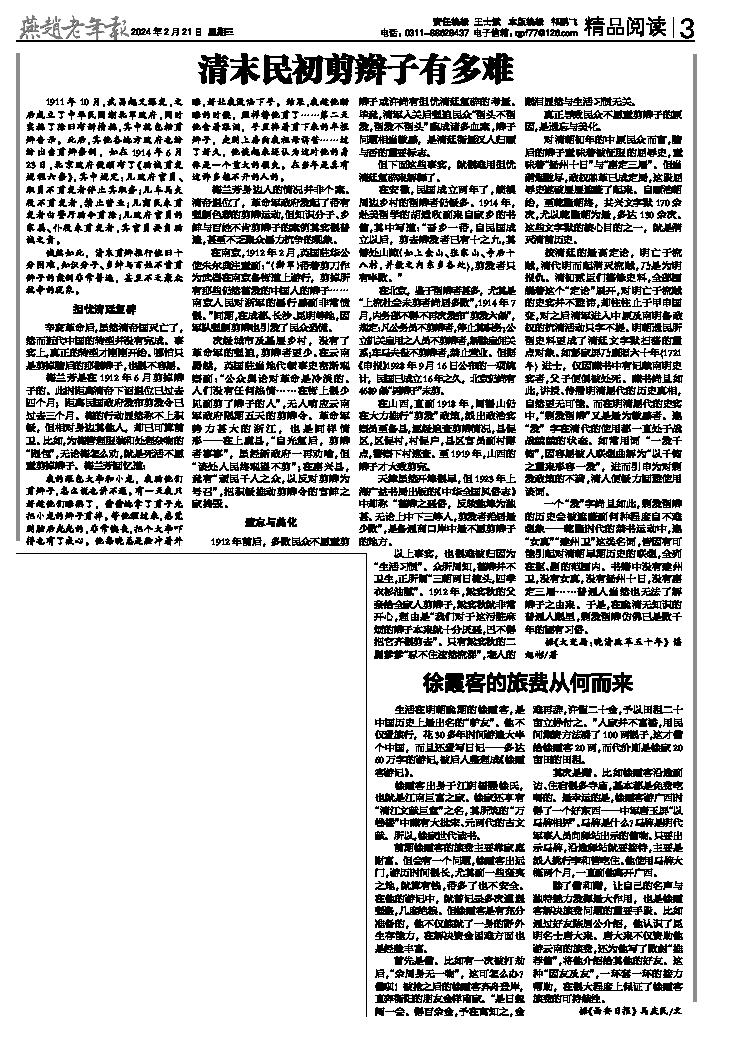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成立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同时实施了除旧布新措施,其中就包括剪辫告示。此后,其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剪辫条例,如在1914年6月23日,北京政府便颁布了《劝诫剪发规程六条》,其中规定:凡政府官员、职员不剪发者停止其职务;凡车马夫役不剪发者,禁止营业;凡商民未剪发者由警厅劝令剪除;凡政府官员的家属、仆役未剪发者,其官员要负劝诫之责。
诚然如此,清末剪辫推行依旧十分困难,知识分子、乡绅与百姓不肯剪辨子的案例非常普遍,甚至不乏聚众抗争的现象。
担忧清廷复辟
辛亥革命后,虽然清帝国灭亡了,然而近代中国的转型并没有完成。事实上,真正的转型才刚刚开始。哪怕只是剪掉脑后的那根辫子,也很不容易。
梅兰芳是在1912年6月剪掉辫子的。此时距离清帝下诏退位已过去四个月;距离民国政府发布剪发令已过去三个月。梅的行动显然称不上积极,但相对身边其他人,却已可算前卫。比如,为梅管理服装和处理杂物的“跟包”,无论梅怎么劝,就是死活不愿意剪掉辫子。梅兰芳回忆道:
我的跟包大李和小龙,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小龙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他每晚总是脸冲着外睡,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谈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
梅兰芳身边人的情况并非个案。清帝退位了,革命军政府发起了带有强制色彩的剪辫运动,但知识分子、乡绅与百姓不肯剪辫子的案例其实很普遍,甚至不乏聚众暴力抗争的现象。
在南京,1912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注意到:“(浙军)带着剪刀作为武器在南京各街道上游行,剪掉所有那些仍然蓄发的中国人的辫子……南京人民对浙军的暴行感到非常愤恨。”同期,在成都、长沙、昆明等地,因军队强制剪辫也引发了民众恐慌。
次级城市及基层乡村,没有了革命军的强迫,剪辫者更少。在云南腾越,英国驻当地代领事史密斯观察到:“公众舆论对革命是冷淡的。人们没有任何热情……在街上很少见到剪了辫子的人”,无人响应云南军政府限期五天的剪辫令。革命军势力甚大的浙江,也是同样情形——在上虞县,“自光复后,剪辫者寥寥”,虽经新政府一再劝喻,但“该处人民终观望不剪”;在嘉兴县,竟有“顽民千人之众,以反对剪辫为号召”,把积极推动剪辫令的官绅之家捣毁。
遗忘与美化
1912年前后,多数民众不愿意剪辫子或许尚有担忧清廷复辟的考量。毕竟,清军入关后强迫民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酿成诸多血案,辫子问题相当敏感,是清廷衡量汉人归顺与否的重要标志。
但下面这些事实,就很难用担忧清廷复辟来解释了。
在安徽,民国成立两年了,绩溪周边乡村的留辫者仍极多。1914年,赴美留学的胡适收到来自家乡的书信,其中写道:“吾乡一带,自民国成立以后,剪去辫发者已有十之九,其僻处山陬(如上金山、张家山、寺后十八村,并歙之内东乡各处),剪发者只有半数。”
在北京,鉴于留辫者甚多,尤其是“上流社会未剪者尚居多数”,1914年7月,内务部不得不再次发布“剪发六条”,规定:凡公务员不剪辫者,停止其职务;公立机关雇用之人员不剪辫者,解除雇佣关系;车马夫役不剪辫者,禁止营业。但据《申报》1928年9月16日公布的一项统计,民国已成立16年之久,北京仍尚有4689条“男辫子”未剪。
在山西,直到1918年,阎锡山仍在大力推行“剪发”政策,派出政治实察员至各县,逐级追查剪辫情况,县促区,区促村,村促户,县区官员到村蹲点,警察下村巡查。至1919年,山西的辫子才大致剪完。
天津虽然开埠很早,但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却称“蓄辫之恶俗,反较他埠为独甚。无论上中下三等人,剪发者殆居最少数”,是各通商口岸中最不愿剪辫子的地方。
以上事实,也很难被归因为“生活习惯”。众所周知,蓄辫并不卫生,正所谓“三朝两日梳头,四季衣衫油腻”。1912年,梁实秋的父亲给全家人剪辫子,梁实秋就非常开心,理由是“我们对于这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只有梁实秋的二舅爹爹“忍不住泫然流涕”,老人的眼泪显然与生活习惯无关。
真正导致民众不愿意剪辫子的原因,是遗忘与美化。
对清朝初年的中原民众而言,脑后的辫子意味着被征服的屈辱史,意味着“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但当硝烟散尽,政权鼎革已成定局,这段屈辱史遂破层层遮蔽了起来。自顺治朝始,至乾隆朝终,共兴文字狱170余次,尤以乾隆朝为最,多达130余次。这些文字狱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消灭清前历史。
按清廷的最高定论,明亡于流贼,清代明而起消灭流贼,乃是为明报仇。清初贰臣们纂修史料,全部围绕着这个“定论”展开,对明亡于流贼的史实并不避讳,却往往止于甲申国变,对之后清军进入中原及南明各政权的抗清活动只字不提。明朝遗民所留史料更成了清廷文字狱扫荡的重点对象。如彭家屏乃康照六十年(1721年)进士,仅因藏书中有记载南明史实者,父子便俱被处死。藏书尚且如此,讲授、传播明清易代的历史真相,自然更无可能。而在明清易代的史实中,“剃发留辫”又是最为敏感者。连“发”字在清代的使用都一直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如常用词“一发千钧”,因容易被人联想曲解为“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发”,进而引申为对剃发政策的不满,清人便极力回避使用该词。
一个“发”字尚且如此,剃发留辫的历史会被遮蔽到何种程度自不难想象——乾隆时代的禁书运动中,连“女真”“建州卫”这类名词,皆因有可能引起对清朝早期历史的联想,全列在抠、删的范围内。书籍中没有建州卫,没有女真,没有扬州十日,没有嘉定三屠……普通人当然也无法了解辫子之由来。于是,在晚清无知识的普通人眼里,剃发留辫仿佛已是数千年的固有习俗。
据《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 谌旭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