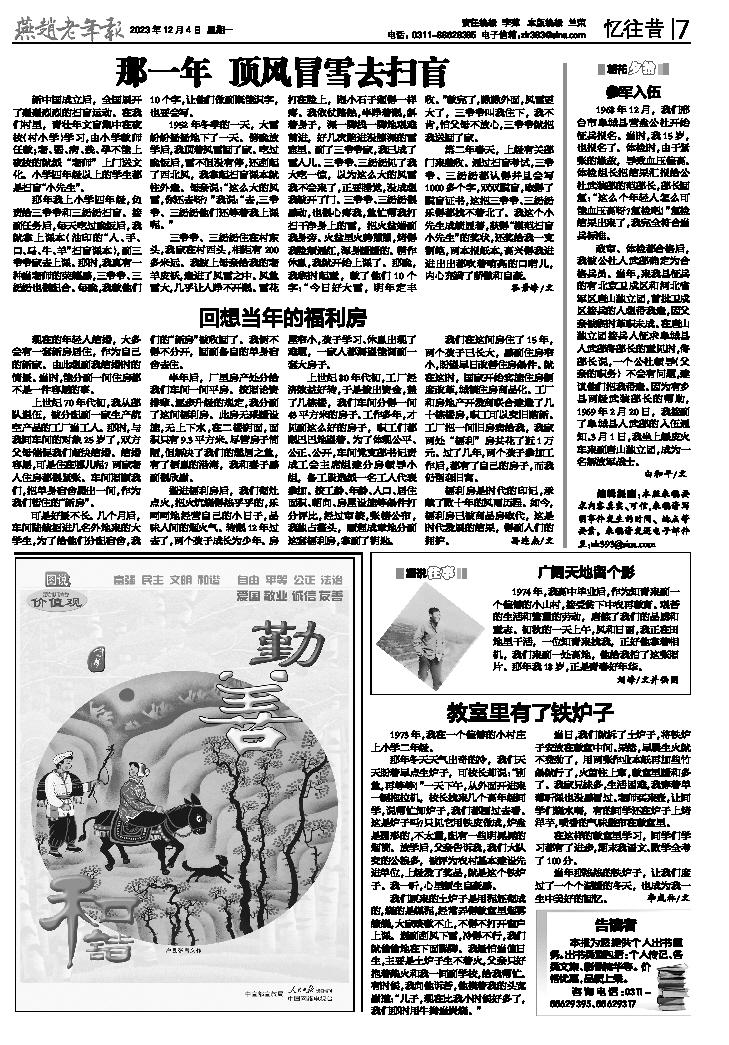1973年,我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上小学二年级。
那年冬天天气出奇的冷,我们天天盼着早点生炉子,可校长却说:“别急,再等等!”一天下午,从外面开进来一辆拖拉机,校长找来几个高年级同学,说帮忙卸炉子,我们都围过去看。这是炉子吗?只见它用铁皮做成,炉盘是圆形的,不太重,配有一些明晃晃的烟筒。放学后,父亲告诉我,我们大队交的公粮多,被评为农村基本建设先进单位,上级发了奖品,就是这个铁炉子。我一听,心里顿生自豪感。
我们原来的土炉子是用泥坯砌成的,烧的是煤泥,经常弄得教室里烟雾缭绕,大家咳嗽不止,不得不打开窗户上课。遇到刮风下雪,冷得不行,我们就偷偷地在下面跺脚。我最怕当值日生,主要是土炉子生不着火,父亲只好抱着柴火和我一同到学校,给我帮忙。有时候,我向他诉苦,他摸着我的头宽慰道:“儿子,现在比我小时候好多了,我们那时用牛粪当炭烧。”
当日,我们就拆了土炉子,将铁炉子安放在教室中间。果然,早晨生火就不费劲了,用两张作业本纸再加些竹条就行了,火苗往上窜,教室里暖和多了。我家兄妹多,生活困难,我穿着单薄听课也没感冒过。老师买来壶,让同学们烧水喝,有的同学还在炉子上烤洋芋,喷香的气味散布在教室里。
在这样的教室里学习,同学们学习都有了进步,期末我语文、数学全考了100分。
当年那热热的铁炉子,让我们度过了一个个温暖的冬天,也成为我一生中美好的回忆。李成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