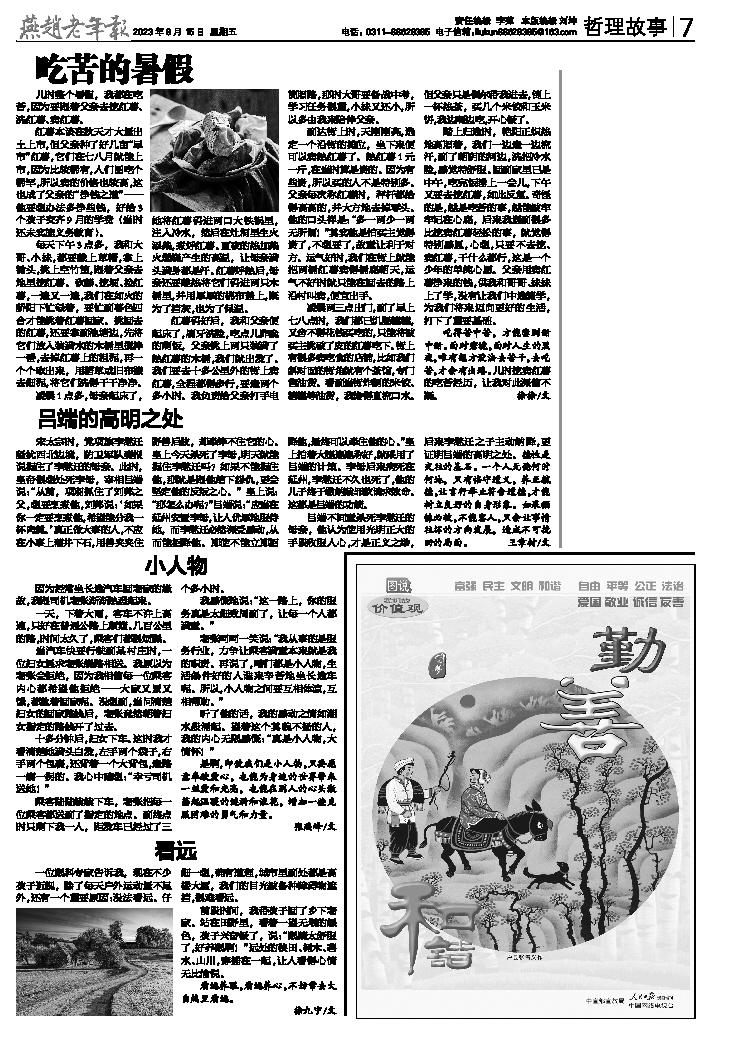儿时整个暑假,我都在吃苦,因为要跟着父亲去挖红薯、洗红薯、卖红薯。
红薯本该在秋天才大量出土上市,但父亲种了好几亩“早市”红薯,它们在七八月就能上市,因为比较稀有,人们图吃个稀罕,所以卖的价格也较高,这也成了父亲的“挣钱之道”——他要想办法多挣些钱,好给3个孩子交齐9月的学费(当时还未实施义务教育)。
每天下午3点多,我和大哥、小妹,都要戴上草帽,拿上锄头,挑上空竹筐,跟着父亲去地里挖红薯。砍藤、挖埂、捡红薯,一遍又一遍,我们在如火的骄阳下忙碌着,要忙到暮色四合才能挑着红薯回家。挑回去的红薯,还要拿到池塘边,先将它们放入装满水的木桶里搅拌一番,去掉红薯上的粗泥,再一个个取出来,用稻草或旧布擦去细泥,将它们洗得干干净净。
凌晨1点多,母亲起床了,她将红薯码进两口大铁锅里,注入冷水,然后在灶洞里生火添柴,煮烀红薯。夏夜的热加柴火燃烧产生的高温,让母亲满头满身都是汗。红薯烀熟后,母亲还要趁热将它们码进两只木桶里,并用厚厚的棉布盖上,既为了挡灰,也为了保温。
红薯码好后,我和父亲便起床了,刷牙洗脸,吃点儿昨晚的剩饭,父亲挑上两只装满了熟红薯的木桶,我们就出发了。我们要去十多公里外的街上卖红薯,全程都得步行,要走两个多小时。我负责给父亲打手电筒照路,那时大哥要备战中考,学习任务很重,小妹又还小,所以多由我来陪伴父亲。
到达街上时,天刚刚亮,选定一个沿街的摊位,坐下来便可以卖熟红薯了。熟红薯1元一斤,在当时算是贵的。因为有些贵,所以买的人不是特别多。父亲每次称红薯时,秤杆都给得高高的,并大方地去掉零头。他的口头禅是:“多一两少一两无所谓!”其实他是怕买主觉得贵了,不想要了,故意让利于对方。运气好时,我们在街上就能把两桶红薯卖得桶底朝天,运气不好时就只能在回去的路上沿村叫卖,便宜出手。
凌晨两三点出门,到了早上七八点时,我们都已饥肠辘辘,又舍不得花钱买吃的,只能将被买主挑破了皮的红薯吃下。街上有很多卖吃食的店铺,比如我们斜对面的街角就有个茶馆,专门售油货。看到当街炸制的米饺、糖糕等油货,我馋得直流口水。但父亲只是偶尔带我进去,倒上一杯热茶,买几个米饺和玉米饼,我边喝边吃,开心极了。
踏上归途时,艳阳正炽热地高照着,我们一边走一边流汗,到了朝阴的河边,洗把冷水脸,感觉特舒服。回到家里已是中午,吃完饭睡上一会儿,下午又要去挖红薯,如此反复。奇怪的是,越是吃苦的事,越能被牢牢记在心底,后来我遇到很多比挖卖红薯轻松的事,就觉得特别感恩,心想,只要不去挖、卖红薯,干什么都行,这是一个少年的单纯心愿。父亲用卖红薯挣来的钱,供我和哥哥、妹妹上了学,没有让我们中途辍学,为我们将来迈向更好的生活,打下了重要基础。
吃得苦中苦,方能尝到甜中甜。面对窘境,面对人生的黑夜,唯有想方设法去苦干,去吃苦,才会有出路。儿时挖卖红薯的吃苦经历,让我对此深信不疑。 徐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