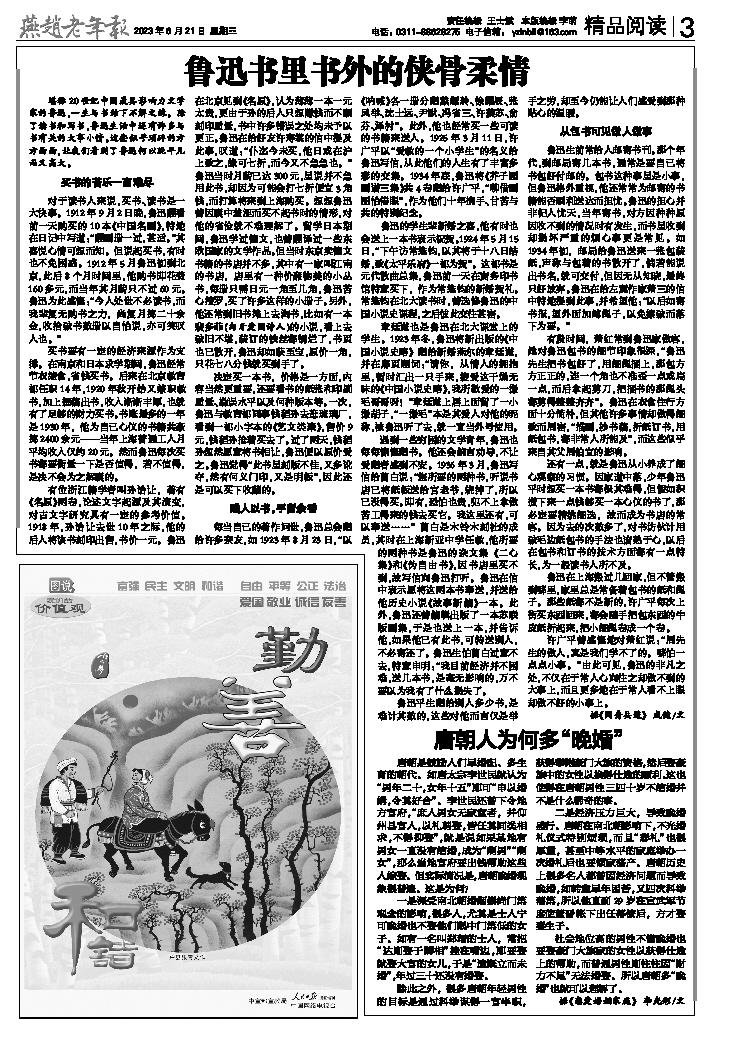堪称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文学家的鲁迅,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除了读书和写书,鲁迅生活中还有许多与书有关的大事小情。这些似乎琐碎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何以既平凡而又高大。
买书的苦乐一言难尽
对于读书人来说,买书、读书是一大快事。1912年9月2日晚,鲁迅翻看前一天购买的10本《中国名画》,特地在日记中写道:“翻画册一过,甚适。”其喜悦心情可想而知。但说起买书,有时也不免困惑。1912年5月鲁迅初到北京,此后8个月时间里,他购书即花费160多元,而当年其月薪只不过60元。鲁迅为此感慨:“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
买书要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作为支撑。在南京和日本求学期间,鲁迅经常节衣缩食,省钱买书。后来在北京教育部任职14年,1920年秋开始又兼职教书,加上撰稿出书,收入渐渐丰厚,也就有了足够的财力买书。书账最多的一年是1930年,他为自己心仪的书籍共豪掷2400余元——当年上海普通工人月平均收入仅约20元。然而鲁迅每次买书都要衡量一下是否值得,若不值得,是决不会为之解囊的。
有位浙江籍学者叫孙诒让,著有《名原》两卷,论述文字起源及其演变,对古文字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918年,孙诒让去世10年之际,他的后人将该书刻印出售,书价一元。鲁迅在北京见到《名原》,认为薄薄一本一元太贵,更由于孙的后人只想赚钱而不顾刻印质量,书中许多错误之处均未予以更正。鲁迅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提及此事,叹道:“仆迄今未买,他日或在沪上致之,缘可七折,而今又不急急也。”鲁迅当时月薪已达300元,虽说并不急用此书,却因为可能会打七折便宜3角钱,而打算将来到上海购买。想想鲁迅曾因囊中羞涩而买不起书时的情形,对他的省俭就不难理解了。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学过德文,也曾翻译过一些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但当时东京卖德文书籍的书店并不多,其中有一家叫江南的书店,店里有一种价廉物美的小丛书,每册只需日元一角至几角,鲁迅苦心搜罗,买了许多这样的小册子。另外,他还常到旧书摊上去淘书,比如有一本裴多菲(匈牙爱国诗人)的小说,看上去破旧不堪,装订的铁丝都锈烂了,书页也已散开,鲁迅却如获至宝,原价一角,只花七八分钱就买到手了。
决定买一本书,价格是一方面,内容当然更重要,还要看书的纸张和印刷质量、勘误水平以及何种版本等。一次,鲁迅与教育部同事钱稻孙去逛琉璃厂,看到一部小字本的《艺文类聚》,售价9元,钱稻孙抢着买去了。过了两天,钱稻孙忽然愿意将书相让,鲁迅便以原价受之。鲁迅觉得“此书虽刻版不佳,又多讹夺,然有何义门印,又是明板”,因此还是可以买下收藏的。
赠人以书,手留余香
每当自己的著作问世,鲁迅总会赠给许多亲友,如1923年8月23日,“以《呐喊》各一册分赠戴螺舲、徐耀辰、张凤举、沈士远、尹默、冯省三、许羡苏、俞芬、泽村”。此外,他也经常买一些可读的书籍来送人。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名义给鲁迅写信,从此他们的人生有了丰富多彩的交集。1934年底,鲁迅将《芥子园画谱三集》共4卷赠给许广平,“聊借画图怡倦眼”,作为他们十年携手、甘苦与共的特别纪念。
鲁迅的学生辈新婚之喜,他有时也会送上一本书表示祝贺。1924年5月15日,“下午访常维钧,以其将于十八日结婚,致《太平乐府》一部为贺”。这部书是元代散曲总集,鲁迅前一天在商务印书馆特意买下,作为常维钧的新婚贺礼。常维钧在北大读书时,曾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之后彼此交往甚密。
章廷谦也是鲁迅在北大课堂上的学生。1923年冬,鲁迅将新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赠给新婚燕尔的章廷谦,并在扉页题词:“请你,从情人的拥抱里,暂时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章廷谦上唇上面留了一小撮胡子,“一撮毛”本是其爱人对他的昵称,被鲁迅听了去,就一直当外号使用。
遇到一些穷困的文学青年,鲁迅也每每慷慨赠书。他还会婉言劝导,不让受赠者感到不安。1936年3月,鲁迅写信给曹白说:“您所要的两种书,听说书店已将纸板送给官老爷,烧掉了,所以已没得买。即有,恐怕也贵,犯不上拿做苦工得来的钱去买它。我这里还有,可以奉送……”曹白是木铃木刻社的成员,其时在上海新亚中学任教,他所要的两种书是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和《伪自由书》,因书店里买不到,故写信向鲁迅打听。鲁迅在信中表示愿将这两本书奉送,并送给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一本。此外,鲁迅还曾编辑出版了一本苏联版画集,于是也送上一本,并告诉他,如果他已有此书,可转送别人,不必寄还了。鲁迅生怕曹白过意不去,特意申明:“我目前经济并不困难,送几本书,是毫无影响的,万不要以为我有了什么损失了。
鲁迅平生赠给别人多少书,是难计其数的,这些对他而言仅是举手之劳,却至今仍能让人们感受到那种贴心的温暖。
从包书可见做人做事
鲁迅生前常给人邮寄书刊。那个年代,到邮局寄几本书,通常是要自己将书包好付邮的。包书这种事虽是小事,但鲁迅格外重视,他还常常为邮寄的书籍能否顺利送达而担忧。鲁迅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当年寄书,对方因种种原因收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书虽收到却损坏严重的烦心事更是常见。如1934年初,邮局给鲁迅送来一张包装纸,声称与包着的书散开了,倘若能说出书名,就可交付,但因无从知晓,最终只好放弃。鲁迅在给左翼作家萧三的信中特地提到此事,并希望他:“以后如寄书报,望外面加缚绳子,以免擦破而落下为要。”
有段时间,萧红常到鲁迅家做客,她对鲁迅包书的细节印象很深,“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起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鲁迅在衣食住行方面十分简朴,但其他许多事情却做得细致而周密,“描画,抄书稿,折纸订书,用纸包书,都非常人所能及”,而这些似乎来自其父周伯宜的影响。
还有一点,就是鲁迅从小养成了细心观察的习惯。因家道中落,少年鲁迅平时想买一本书都极其难得,但假如积攒下来一点钱够买一本心仪的书了,那必定要精挑细选,故而成为书店的常客。因为去的次数多了,对书坊伙计用破毛边纸包书的手法也谙熟于心,以后在包书和订书的技术方面都有一点特长,为一般读书人所不及。
鲁迅在上海搬过几回家,但不管搬到哪里,家里总是常备着包书的纸和绳子。那些纸都不是新的,许广平每次上街买东西回来,都会随手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把小细绳卷成一个卷。
许广平曾感慨地对萧红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由此可见,鲁迅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常人心向往之却做不到的大事上,而且更多地在于常人看不上眼却做不好的小事上。
据《同舟共进》 成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