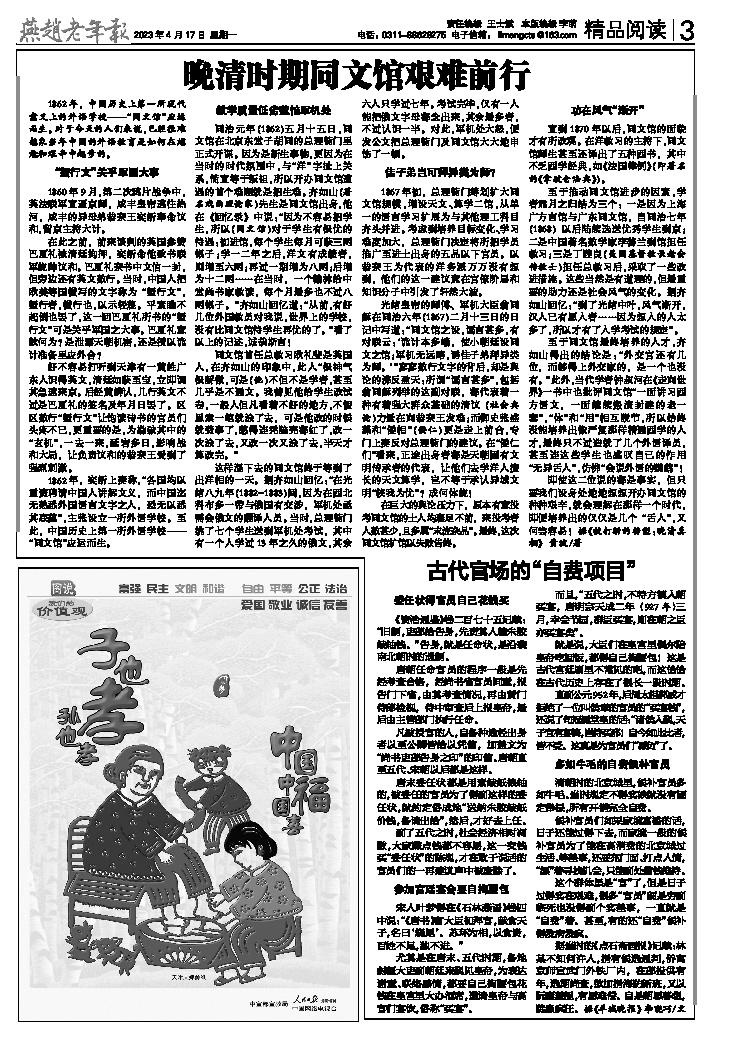1862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外语学校——“同文馆”应运而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很难想象当年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如何在尴尬和艰辛中起步的。
“蟹行文”关乎军国大事
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直逼京师,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咸丰的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奉命议和,留京主持大计。
在此之前,前来谈判的英国参赞巴夏礼被清廷拘押,奕訢命他致书联军统帅议和。巴夏礼亲书中文信一封,但旁边还有英文数行。当时,中国人把欧美等国横写的文字称为“蟹行文”,蟹行者,横行也,以示轻蔑。平素瞧不起倒也罢了,这一回巴夏礼所书的“蟹行文”可是关乎军国之大事。巴夏礼意欲何为?是泄露天朝机密,还是授以诡计准备里应外合?
好不容易打听到天津有一黄姓广东人识得英文,清廷如获至宝,立即调其急速来京。后经黄辨认,几行英文不过是巴夏礼的签名及年月日罢了。区区数行“蟹行文”让饱读诗书的官员们头疼不已,更重要的是,为勘破其中的“玄机”,一去一来,延宕多日,影响战和大局,让负责议和的恭亲王受到了强烈刺激。
1862年,奕訢上奏称,“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主张设立一所外语学校。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应运而生。
教学质量低劣惹恼军机处
同治元年(1862)五月十五日,同文馆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里正式开课。因为是新生事物,更因为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与“洋”字扯上关系,简直等于叛祖,所以开办同文馆遭遇的首个难题就是招生难。齐如山(著名戏曲理论家)先生是同文馆出身,他在《回忆录》中说:“因为不容易招学生,所以(同文馆)对于学生有极优的待遇:初进馆,每个学生每月可获三两银子;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后增为十二两……在当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个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齐如山回忆道:“从前,有好几位外国教员对我说,世界上的学校,没有比同文馆待学生再优的了。”看了以上的记述,诚哉斯言!
同文馆首任总教习欧礼斐是英国人,在齐如山的印象中,此人“极神气极骄傲,可是(他)不但不是学者,甚至几乎是不通文。我曾见他给学生改试卷,一般人但凡看着不好的地方,不假思索一笔就涂了去,可是他改的时候就费事了,憋得连秃脑壳都红了,改一次涂了去,又改一次又涂了去,半天才算改完。”
这样混下去的同文馆终于等到了出洋相的一天。据齐如山回忆:“在光绪八九年(1882-1883)间,因为在西北科布多一带与俄国有交涉,军机处亟需会俄文的翻译人员。当时,总理衙门挑了七个学生送到军机处考试,其中有一个人学过13年之久的俄文,其余六人只学过七年。考试完毕,仅有一人能把俄文字母都念出来,其余最多者,不过认识一半。对此,军机处大怒,便发公文把总理衙门及同文馆大大地申饬了一顿。
佳子弟岂可拜异类为师?
1867年初,总理衙门筹划扩大同文馆规模,增设天文、算学二馆,从单一的语言学习扩展为与其他理工科目齐头并进。考虑到培养目标变化、学习难度加大,总理衙门决定将所招学员推广至进士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以恭亲王为代表的洋务派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一建议竟在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中引发了轩然大波。
光绪皇帝的师傅、军机大臣翁同龢在同治六年(1867)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寥寥数行文字的背后,却是舆论的沸反盈天:所谓“谣言甚多”,包括翁同龢列举的这副对联,都代表着一种有着强大群众基础的清议(社会典论)力量在向恭亲王发难;而御史张盛藻和“倭相”(倭仁)更是走上前台,专门上奏反对总理衙门的建议。在“倭仁们”看来,正途出身者都是天朝固有文明传承者的代表,让他们去学洋人擅长的天文算学,岂不等于承认异域文明“较我为优”?成何体统!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原本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士人均裹足不前,来投考者人数甚少,且多属“末流杂品”。最终,这次同文馆扩馆以失败告终。
功在风气“渐开”
直到1870年以后,同文馆的面貌才有所改观。在洋教习的主持下,同文馆师生甚至还译出了五种西书,其中不乏西学经典,如《法国律例》(即著名的《拿破仑法典》)。
至于推动同文馆进步的因素,学者熊月之归结为三个:一是因为上海广方言馆与广东同文馆,自同治七年(1868)以后陆续选送优秀学生到京;二是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到馆担任教习;三是丁韪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担任总教习后,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这些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最重要的助力还是社会风气的变化。据齐如山回忆:“到了光绪中叶,风气渐开,汉人已有愿入者……因为想入的人太多了,所以才有了入学考试的规定”。
至于同文馆最终培养的人才,齐如山得出的结论是:“外交官还有几位,而够得上外交家的,是一个也没有。”此外,当代学者钟叔河在《走向世界》一书中也批评同文馆“一面讲习西方语文,一面继续搬演封建的老一套”,“体”和“用”相互脱节,所以始终没能培养出像严复那样精通西学的人才,最终只不过造就了几个外语译员,甚至连这些学生也感叹自己的作用“无异舌人”,仿佛“会说外语的鹦鹉”!
即使这二位说的都是事实,但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想开办同文馆的种种艰辛,就会理解在那样一个时代,即便培养出的仅仅是几个“舌人”,又何尝容易!据《被打断的转型:晚清真相》 黄波/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