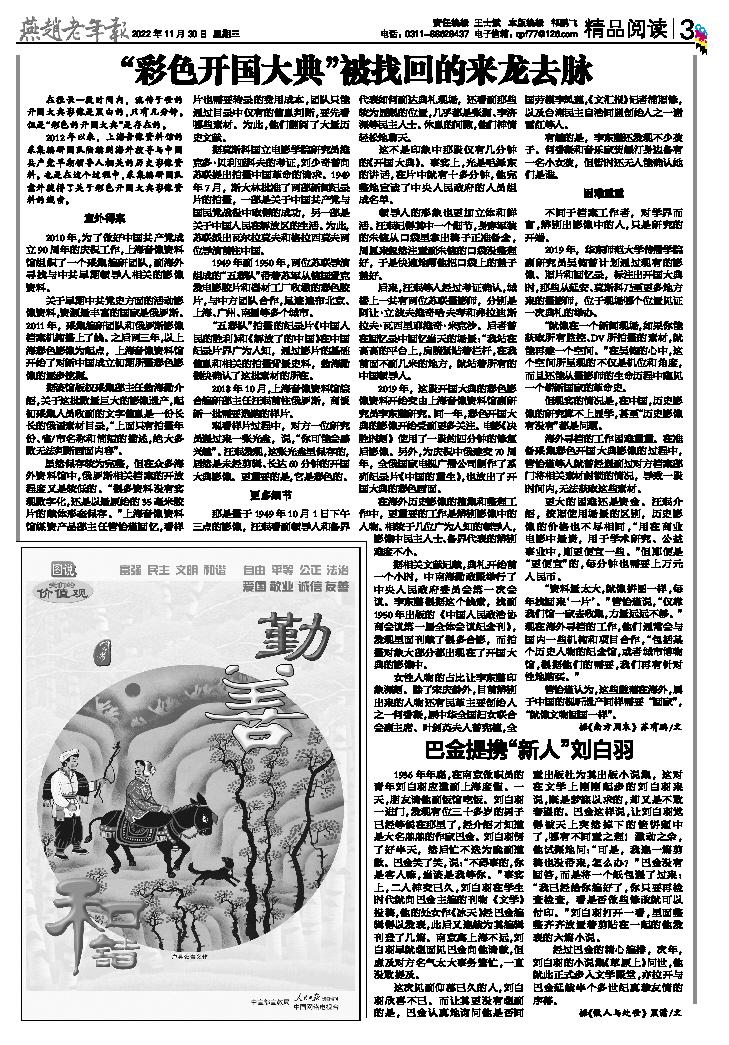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流传于世的开国大典影像是黑白的,只有几分钟。但是“彩色的开国大典”是存在的。
2012年以来,上海音像资料馆的采集编研团队陆续到海外搜寻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相关的历史影像资料。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采集编研团队意外获得了关于彩色开国大典影像资料的线索。
意外得来
2010年,为了做好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庆祝工作,上海音像资料馆组织了一个采集编研团队,到海外寻找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相关的影像资料。
关于早期中共党史方面的活动影像资料,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是俄罗斯。2011年,采集编研团队和俄罗斯影像档案机构搭上了线。之后两三年,以上海彩色影像为起点,上海音像资料馆开始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摄彩色影像的逐步挖掘。
据该馆版权采集部主任翁海勤介绍,关于这批数量巨大的影像遗产,起初采集人员收到的文字信息是一份长长的俄语素材目录,“上面只有拍摄年份、省/市名称和简短的描述,绝大多数无法判断画面内容”。
虽然保存较为完整,但在众多海外资料馆中,俄罗斯相关档案的开放程度又是较低的。“很多资料没有实现数字化,还是以最原始的35毫米胶片的载体形态保存。”上海音像资料馆媒资产品部主任管怡瑾回忆,看样片也需要转录的费用成本,团队只能通过目录中仅有的信息判断,要先看哪些素材。为此,他们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
据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研究员维克多·贝利亚科夫的考证,刘少奇曾向苏联提出拍摄中国革命的请求。1949年7月,斯大林批准了两部新闻纪录片的拍摄,一部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战役中取得的成功,另一部是关于中国人民在解放区的生活。为此,苏联派出瓦尔拉莫夫和格拉西莫夫两位导演前往中国。
1949年到1950年,两位苏联导演组成的“五彩队”带着苏军从德国爱克发电影胶片和器材工厂收缴的彩色胶片,与中方团队合作,足迹遍布北京、上海、广州、南昌等多个城市。
“五彩队”拍摄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在中国纪录片界广为人知,通过影片的基础信息和相关的拍摄背景史料,翁海勤很快确认了这批素材的所在。
2018年10月,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汪珉前往俄罗斯,商谈新一批需要选购的样片。
观看样片过程中,对方一位研究员递过来一张光盘,说,“你可能会感兴趣”。汪珉发现,这张光盘里保存的,居然是未经剪辑、长达60分钟的开国大典影像。更重要的是,它是彩色的。
更多细节
那是摄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的影像,汪珉看到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如何到达典礼现场,还看到那些较为显眼的位置,几乎都是张澜、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休息的间隙,他们神情轻松地聊天。
这不是印象中那段仅有几分钟的《开国大典》。事实上,光是毛泽东的讲话,在片中就有十多分钟,他完整地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名单。
领导人的形象也更加立体和鲜活。汪珉记得其中一个细节,身穿军装的朱德从口袋里拿出稿子正准备念,周恩来忽然注意到朱德的口袋没整理好,于是快速地帮他把口袋上的盖子盖好。
后来,汪珉等人经过考证确认,城楼上一共有两位苏联摄影师,分别是阿让·立波夫维奇哈夫琴和弗拉迪斯拉夫·瓦西里耶维奇·米克沙。后者曾在回忆录中回忆当天的场景:“我站在高高的平台上,肩膀紧贴着栏杆,在我前面不到几米的地方,就站着所有的中国领导人。
2019年,这段开国大典的彩色影像资料开始交由上海音像资料馆副研究员李东鹏研究。同一年,彩色开国大典的影像开始受到更多关注。电影《决胜时刻》使用了一段约四分钟的修复后影像。另外,为庆祝中俄建交70周年,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制作了系列纪录片《中国的重生》,也放出了开国大典的彩色画面。
在海外历史影像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中,更重要的工作是辨别影像中的人物。相较于几位广为人知的领导人,影像中民主人士、各界代表的辨别难度不小。
据相关文献记载,典礼开始前一个小时,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李东鹏根据这个线索,找到1950年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发现里面刊载了很多合影,而拍摄对象大部分都出现在了开国大典的影像中。
女性人物的占比让李东鹏印象深刻。除了宋庆龄外,目前辨别出来的人物还有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何香凝,原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叶剑英夫人曾宪植,全国劳模李凤莲,《文汇报》记者浦照修,以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始人之一谢雪红等人。
有趣的是,李东鹏还发现不少孩子。何香凝和音乐家贺绿汀身边各有一名小女孩,但暂时还无人能确认她们是谁。
困难重重
不同于档案工作者,对学界而言,辨别出影像中的人,只是研究的开端。
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员吴钧曾计划通过现有的影像、照片和回忆录,标注出开国大典时,那些从延安、莫斯科乃至更多地方来的摄影师,位于现场哪个位置见证一次典礼的举办。
“就像在一个新闻现场,如果你能获取所有监控、DV所拍摄的素材,就能再建一个空间。”在吴钧的心中,这个空间所呈现的不仅是机位和角度,而且还能从摄影师的生命历程中窥见一个崭新国家的革命史。
但现实的情况是,在中国,历史影像的研究算不上显学,甚至“历史影像有没有”都是问题。
海外寻档的工作困难重重。在准备采集彩色开国大典影像的过程中,管怡瑾等人就曾经遇到过对方档案部门将相关素材封锁的情况,导致一段时间内,无法获取这些素材。
更大的困难还是资金。汪珉介绍,按照使用场景的区别,历史影像的价格也不尽相同,“用在商业电影中最贵,用于学术研究、公益事业中,则更便宜一些。”但即便是“更便宜”的,每分钟也需要上万元人民币。
“资料量太大,就像拼图一样,每年找回来‘一片’。”管怡瑾说,“仅靠我们馆一家去收集,力量远远不够。”现在海外寻档的工作,他们通常会与国内一些机构和项目合作,“包括某个历史人物的纪念馆,或者城市博物馆,根据他们的需要,我们再有针对性地购买。”
管怡瑾认为,这些散落在海外,属于中国的视听遗产同样需要“回家”,“就像文物回国一样”。
据《南方周末》 苏有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