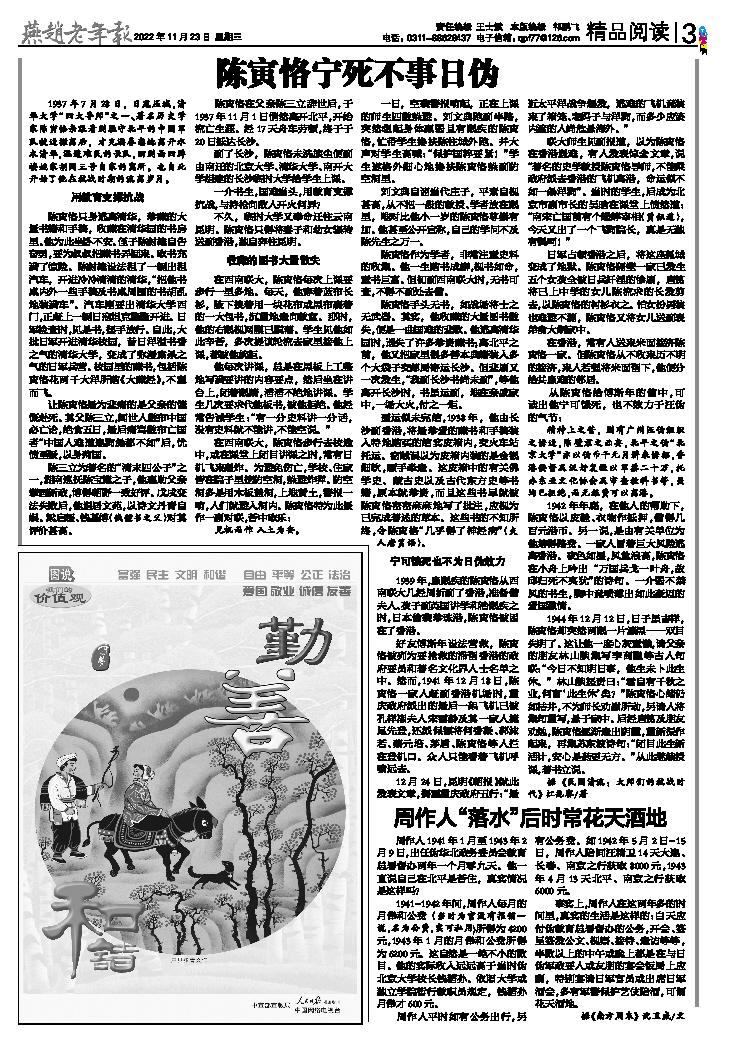1937年7月28日,日寇压城,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亲眼看到驻守北平的中国军队被迫撤离后,才充满眷恋地离开水木清华,混进难民的长队,回到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自家的寓所。也自此开始了他在抗战时期的流离岁月。
用教育支撑抗战
陈寅恪只身逃离清华,珍藏的大量书籍和手稿,收藏在清华园的书房里。他为此坐卧不安。侄子陈封雄自告奋勇,要为叔叔把藏书弄回来。取书充满了惊险。陈封雄设法租了一辆出租汽车,开进冷冷清清的清华,“把他书桌内外一些手稿及书桌周围的书胡乱地装满车”。汽车刚要出清华大学西门,正赶上一辆日寇坦克隆隆开进。日军检查时,见是书,摆手放行。自此,大批日军开进清华校园,昔日洋溢书香之气的清华大学,变成了弥漫肃杀之气的日军兵营。校园里的藏书,包括陈寅恪花两千大洋所购《大藏经》,不翼而飞。
让陈寅恪最为悲痛的是父亲的慷慨赴死。其父陈三立,闻世人散布中国必亡论,绝食五日,最后痛骂散布亡国者“中国人难道连狗彘都不如”后,忧愤至极,以身殉国。
陈三立为著名的“清末四公子”之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他襄助父亲擘画新政,博得朝野一致好评。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退居文苑,以诗文丹青自娱。梁启超、钱基博(钱锺书之父)对其评价甚高。
陈寅恪在父亲陈三立辞世后,于1937年11月1日悄然离开北平,开始流亡生涯。经17天舟车劳顿,终于于20日抵达长沙。
到了长沙,陈寅恪未洗旅尘便到由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给学生上课。
一介书生,国难当头,用教育支撑抗战,与持枪向敌人开火何异?
不久,临时大学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陈寅恪只得将妻子和幼女辗转送到香港,独自奔往昆明。
收藏的图书大量散失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每次上课要步行一里多地。每天,他穿着蓝布长衫,腋下挟着用一块花布或黑布裹着的一大包书,沉重地走向教室。那时,他的右眼视网膜已脱落。学生见他如此辛苦,多次提议轮流去家里接他上课,都被他婉拒。
他每次讲课,总是在黑板上工整地写满要讲的内容要点,然后坐在讲台上,闭着眼睛,滔滔不绝地讲课。学生几次要求代他板书,被他拒绝。他经常告诫学生:“有一分史料讲一分话,没有史料就不能讲,不能空说。”
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步行去校途中,或在课堂上闭目讲课之时,常有日机飞来轰炸。为避免伤亡,学校、住家皆在院子里挖防空洞,躲避炸弹。防空洞多是用木板盖洞,上堆黄土,警报一响,人们就避入洞内。陈寅恪特为此景作一副对联,苦中取乐: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
一日,空袭警报响起,正在上课的师生四散躲避。刘文典跑到半路,突然想起身体羸弱且有眼疾的陈寅恪,忙带学生搀扶陈往城外跑。并大声对学生高喊:“保护国粹要紧!”学生遂格外细心地搀扶陈寅恪躲到防空洞里。
刘文典自诩当代庄子,平素自视甚高,从不把一般的教授、学者放在眼里,唯对比他小一岁的陈寅恪尊崇有加。他甚至公开宣称,自己的学问不及陈先生之万一。
陈寅恪作为学者,非常注意史料的收集。他一生购书成癖,视书如命,意书巨富。但初到西南联大时,无书可查,不得不到处去借。
陈寅恪手头无书,如战场将士之无武器。其实,他收藏的大量图书散失,便是一曲国难的悲歌。他逃离清华园时,遗失了许多珍贵藏书;离北平之前,他又把家里很多善本典籍装入多个大袋子交邮局寄运长沙。但悲剧又一次发生,“我到长沙书尚未到”,等他离开长沙时,书虽运到,堆在亲戚家中,一场大火,付之一炬。
噩运似未完结,1938年,他由长沙到香港,将最珍爱的藏书和手稿装入特地购买的结实皮箱内,交火车站托运。窃贼误以为皮箱内装的是金银细软,顺手牵走。这皮箱中的有关佛学史、蒙古史以及古代东方史等书籍,原本就珍贵,而且这些书早就被陈寅恪密密麻麻地写了批注,应视为已完成著述的草本。这些书的不知所终,令陈寅格“几乎得了神经病”(夫人唐筼语)。
宁可饿死也不为日伪效力
1939年,患眼疾的陈寅恪从西南联大几经周折到了香港,准备偕夫人、孩子到英国讲学和治眼疾之时,日本偷袭珍珠港,陈寅恪被困在了香港。
好友傅斯年设法营救,陈寅恪被列为要抢救的滞留香港的政府要员和著名文化界人士名单之中。然而,1941年12月18日,陈寅恪一家人赶到香港机场时,重庆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已被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及其一家人捷足先登,还派保镖将何香凝、郭沫若、蔡元培、茅盾、陈寅恪等人拦在登机口。众人只能看着飞机呼啸远去。
12月24日,昆明《朝报》就此发表文章,揭露重庆政府丑行:“最近太平洋战争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子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联大师生见到报道,以为陈寅恪在香港遇难,有人发表悼念文章,说“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当时的学生,后成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课堂上愤然道:“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
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将这座孤城变成了地狱。陈寅恪隔壁一家已发生五个女孩全被日兵奸淫的惨剧,唐筼将已上中学的女儿陈流求的长发剪去,以陈寅恪的衬衫衣之。怕女扮男装也难避不测,陈寅恪又将女儿送到表弟俞大纲家中。
在香港,常有人送来米面接济陈寅恪一家。但陈寅恪从不收来历不明的接济,来人若强将米面留下,他便分给共患难的邻居。
从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可读出他宁可饿死,也不效力于汪伪的气节:
精神上之苦,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诱迫,陈壁君之凶妄,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托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
1942年年底,在他人的帮助下,陈寅恪以皮鞋、衣物作抵押,借得几百元港币。另一说,是由有关单位为他筹得路费。一家人冒着巨大风险逃离香港。夜色如墨,风急浪高,陈寅恪在小舟上吟出“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一介弱不禁风的书生,胸中竟喷薄出如此豪迈的爱国激情。
1944年12月12日,日子虽吉祥,陈寅恪却突然两眼一片漆黑——双目失明了。这让他一度心灰意懒,请父亲的朋友林山腴集写李商隐等古人句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休。”林山腴怒责曰:“君自有千秋之业,何言‘此生休’矣?”陈寅恪心绪仍如枯井,不为师长劝慰所动,另请人将集句重写,悬于家中。后经唐筼及朋友劝勉,陈寅恪逐渐走出阴霾,重新振作起来,再集苏东坡诗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从此继续授课,著书立说。
据《民国清流:大师们的抗战时代》 江兆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