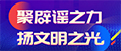1983年4月22日,82岁的林巧稚与世长辞。这年春天,她因为病情恶化,已陷入昏迷多时。值班护士们常常被林巧稚在昏迷中的喊叫声惊醒。有时候她“啊!啊!”地高声叫喊,然后又抱歉地低语“你来得太晚了,只能手术了……有时候,她着急地说:“快!快!拿产钳来!产钳!”护士们会随手拿起身边的一件东西递在她的手里,她抓得很紧。还有的时候,她很高兴:“多可爱的胖姓娃。”作为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林巧稚一生未婚未育,却获得了“万婴之母”的尊称。
叮嘱邓颖超不要挂专家号
1929年,林巧稚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获得毕业生的最高荣誉“文海奖”。“文海奖”每届只授予一人。评选的时侯,校委会曾有过小小的争执。就成绩论,林巧稚比另一位男同学高出1.5分。有人说,男学生对协和的贡献必定超过女学生,他们成绩也差不多。最终决定乾坤的是一位先生的话,他说:林巧稚课余为公益活动尽了许多义务,她为人热诚、有爱心,这是从医人的根本。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协和医院因日军占领而关闭。林巧稚在东堂子胡同10号开设了一家诊所。那6年时间,她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底层民众。北平城里妇产科诊所的门诊挂号费最少是五角,半袋面粉的价钱。她将挂号费降为三角,还在出诊包里常备一些钱,周济那些一贫如洗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第一次到协和找林巧稚看病。林巧稚并不知道她是总理夫人,叮嘱她,以后不要挂专家号,要多花许多钱,她本人也看普通门诊。
有一次林巧稚问她的朋友、朱德夫人康克清:“你开始来看病时也用这个名字吗?”康克清感慨:“可见她在看病时只关心病的本身,并不注意那个病人是谁。”著名妇产科专家叶惠方教授是林巧稚的学生。她记得,在门诊,如果看到哪个病人表情痛苦,林巧稚就会丢下手里的所有事情,直奔这个病人而去。有时候,叶惠方会提醒她,待诊室里有早已约定等候在那里的“特殊病人”。林巧稚总是头也不回地说:“病情重才是真正的特殊。”
上世纪60年代,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刚进入协和医院工作,是林巧稚把他留在了妇产科。他记得,林巧稚位于东单的家里有一部电话,科里有问题打过去请教,事无巨细,她从不厌烦,从不敷衍。一旦觉得电话里说不清楚,她就直接到医院来,无论盛暑严冬、刮风下雨或者深更半夜。
大家都觉得林巧稚身上有种神奇的魔力,不论病人多么惊慌失措,只要她一现身,她们就能平静下来。这种魔力,在她的一言一语、举手投足之间。作为专家,她会把耳朵贴在病人的肚皮上,她还总是摸摸病人的头,掖掖病人的被角,擦擦她们额头上的汗,拉拉她们的手。她出门诊,从不会三言两语打发病人。“医生给人看病不是修理机器,医生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她常对下级医生说,“她们各自的生活背景、思想感情、致病原因各不相同,我们不能凭经验或检验报告就下诊断开处方。”
亲手编写科普读物
冰心的三个孩子,都是林巧稚接生的。她注意到,林巧稚会在每个孩子的出生证上留下流利的英文签名:“ Lin Qiaozhi's Baby”(林巧稚的孩子)。
林巧稚一生的奋斗目标是“让所有的母亲都高兴平安,让所有的孩子都聪明健康”,她并不只在协和医院的病床和手术台前追求这个目标。
1958年,在“大放卫星”的喧嚣声中,医院领导提出要紧跟时代,改进手术洗手方法:洗个手要那么多程序,慢吞吞还怎么“大跃进”?没人敢出来反对,林巧稚直接找到医院领导发问:如果是给你做手术,你要我们洗三遍手还是洗一遍?一次洗五分钟,还是三分钟?
1965年,医院的专家们被组成“巡回医疗队”,派到农村工作。临行前,林巧稚做了准备,她找人了解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当她得知湘阴一带多发眼病,专门抽空到眼科去学习,了解一些眼科常见病的治疗方法。她还找中医大夫学习针灸,学会了头痛、关节痛的针灸疗法。
林巧稚有一句名言:“妊娠保健不是病,妊娠要防病。”多年的从医经历让她深刻意识到,中国妇女的疾病和痛苦很多是因为贫穷、多子女和缺乏起码的卫生常识所致。根据湘阴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况,作为最高专家,林巧稚亲手编写了最通俗的科普读物《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这个科普的任务她一直记在心上。1978年末,她因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入院治疗,还在病床上主持了《家庭卫生顾问》一书的编写。她每天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很多是对一些生理、病理常识问题的咨询,她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深入浅出的解答。之后,她又组织编写了《家庭育儿百科全书》《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在那个时代,这些书成了许多年轻妈妈的必读书,真正成了她们的“家庭卫生顾问”。
留下沉甸甸的遗产
1961年初夏,周恩来和邓颖超邀请林巧稚在一家饭馆吃饭。周恩来关切地对林巧稚说,听说林大夫主动要求降低了自己的口粮,医生的工作任务很重,还是要实事求是,注意身体。当时,林巧稚本来每个月有26斤粮食的定额,她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定量降为16斤。面对周恩来的好意提醒,林巧稚回答,她本来饭量就小,又没有什么负担,希望年轻的医生和护士能够得到更多的关照。
困难时期,医学微生物学专家谢少文因被停职停薪,生活陷入绝境,林巧稚悄悄给他送去一笔钱。为了避免他难堪,她用英文附上句话: It' s not money.lt' s friendship.(这不是钱,这是友谊。)
“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并不怕死。”1980年住院后,林巧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平静地说,“人们了解我,我更了解自己。我没有负疚,没有牽挂,没有悔恨,尽可以暝目而去。”
林巧稚一生没有孩子,但她知道,做了母亲的人,总要花很多心思在孩子身上。平日里,她对妇产科那些有了孩子的年轻同事,总是格外多一些关心和体贴。许多女医生都记得,林巧稚每次向来宾介绍她们时,往往会加上一句:“她还是一位母亲。”
林巧稚有两个存折:一张存着她工资节余的部分;另一张存着工资外的一些收入,比如人大政协开会的补助,还有作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定期发给的车马费。她认为,前笔钱是她的劳动所得,可以用来资助亲成朋友,而后一笔钱则应该另有所用。她留下了自己的遗嘱:3万元积蓄全部捐献给协和医院的托儿所,解决协和母亲们的后顾之优。她的遗体供医院作医学解剖之用,她的骨灰撒在大海上。
据《三联生活周刊》 徐菁菁/文